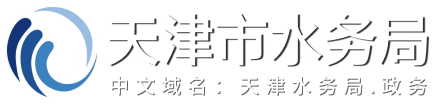关于小站和小站稻的种植历史,百多年来议论很多,特别是建国后,有人将小站种植水稻的种植历史,向前推至宋端拱二年(即公元989年)①。但是小站这个地名,是清同治十年(即公元1871年)才有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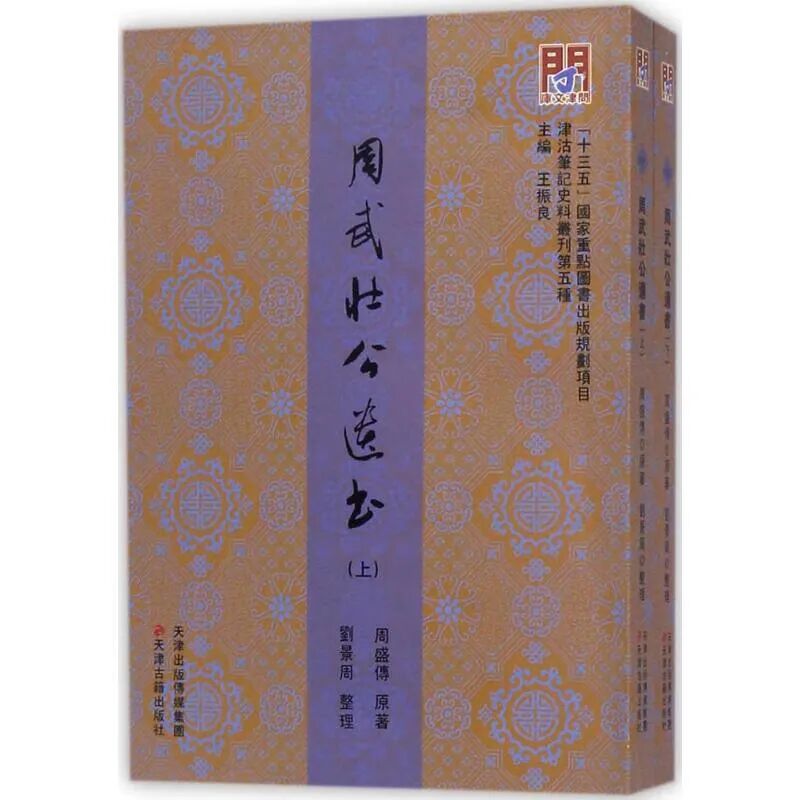
《周武壮公遗书》卷七·屯政编·《覆陈屯政情形禀》中有言:“盛传自从事新城,往来津、静南洼之交,见海河两岸空廓百余里,弃为沮洳。”说明这一地区当年为斥卤不毛之地,人烟罕至。即使葛沽、北塘自明·万历以来屯兵垦荒,但只有葛沽一带有居民引水种稻。“窃尝咨嗟太息,以为海潮一日两至,天然穿引溉田之资,而土人不知引借之方,深为可惜!”“窃尝就海河南岸略加测步,除去极东滨海下游,由咸水沽至高家岭,长约百里,广约十里,计算可耕之田已不下五十余万亩,就中开河筑堤,略仿南人圩田办法,广置闸涵,就上游节节引水放下,以时闭泄田中积卤,常有甜水冲刷自可涤除净尽,变为膏腴。”
另据《周武壮公遗书》卷七·屯政编·《开河兴屯请借米价禀》中说:“窃尝咨考旧闻相度形势,以为欲灌溉新城附近之田,非在咸水沽建闸,增挑引河导之东下以资浇灌不可;欲大垦海河南岸之荒,非由南运河建闸,另辟减河分溜下注以涤积卤不可。盖水势太平,则游波宽缓,冲荡之力亦微。惟自高趋下,势若建瓯,引溜之势捷,故刷咸之力猛,乃能去咸留淤渐成沃壤,此水土之性固然。而南运河会漳河浊流,本有石水斗泥之喻,其肥犹可化碱为腴。”
这是150年前,周盛传身在马厂大营,经多次实地踏勘步测之后,高瞻远瞩得出的结论。并决定“卑军半月后拔至新城,拟先将咸水沽下引河先行挑挖,达于新城外河,分注各沟。宽约五丈,深约丈余,拉长四十余里,每营摊作二里许,约须五十余日竣工。”
“又附城营垒,上年仓猝布扎,但取便于作工,逼城而势,甚局促。现在拓地,渐南就耕不便,拟于距城十余里,贴近新道小站旁,择定空廓大营基一所,现派弁分投搬运砖木物料,拟到新城后即率诸将踹定地址,分筑墙垒、营房,星碁联布,与新城遥连一片,以张远势。”②
就周盛传《开河兴屯请借米价禀》中有“上年仓猝布扎,但取便于作工,逼城而势,甚局促”而言,此禀时间当为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上年“仓猝布扎”是因为日军借口琉球船民在台湾被杀,公然派兵入侵台湾,清政府一方面命沈葆桢派兵增援台湾守军,一方面命李鸿章加强大沽口防御。李鸿章遂命屯兵于马厂的周盛传部前出至新城,增建炮台,以为大沽后援。后经英国公使威妥玛的调停,中日两国签署《台事专约》,日军才全部撤离台湾。
周盛传并非因战事稍缓而懈怠,他枕戈待旦,厉兵秣马,向李鸿章建议,将盛军大营迁到小站一带。剑阁峥嵘,万夫莫开。距今150年矣。
小站初无村落,一片不毛,为沧海之退。周武壮公率盛军在此屯田练兵,垦地五百余顷,凿减河,筑沟渠,斥卤尽成肥沃,什长以上军官尽有养家地。后因中日甲午海战,清军溃败,盛军遣散,小站营田遂转交营田局招租。后袁世凯在此练新建陆军,就食小站,培养出无数骁勇战将,撑起中国半壁江山。
据1931年1月27日大公报所载津郊调查之十《如此之小站》中介绍,说小站镇面积为398方里,辖35个村,有3674户,11632口人。农产品以稻米为大宗,本年每石160斤,售价16元,比临近之葛沽稻米贵一元,且质量最佳。其次为江米,再次为日本稻米。稻地所产螃蟹,以天津、北平、上海为主要营销地,且出口为日本所需之美食。河鱼、港鱼,行销天津及本地。

小站的旱田只占十分之一,减河南岸多细杆苇子(上图),行销日本,批成细笺后做草帽用。麦秆、稻草则销到咸水沽做纸板子。
小站的农民分三类,营田边上有少许民田,是为自耕农。直接租营田者为“大租”,又称官租,每年每亩租价平均一元,肥料、种子、人工、牲畜、农具,每亩需资本二十元。大租户有转租权,以地质肥瘠有差,租价不等。得租权者为“小租”,亦名私租。此外有祠田、学田。“祠田者,周武壮公祠、李鸿章祠田也”。
“小站者,一南腔北调、风俗各别、五方杂处也。前此安徽籍者多数,其他省份人次之,现在以河北各县人为多,安徽次之。再次则湖南、湖北、福建、山东等,多数是军人落籍者,其户口之活动,直天津县之巴黎也。”③
当时小站这地方也有街市,也有工厂,如德商机器煤油铁工厂,专造铜铁机件及什物。小站这地方也有学校,学生多为客籍,虽然有营田附加捐及租官苇湖基金,上学免费,但一发生特殊情况,如兵荒马乱或军队调动,学生照样退学。
小站这地方也有游戏场和落子馆,也有蹦蹦儿、评词、说书的,都得自己下台敛钱,每次二枚铜子。小站这地方也有抽白面、抽大烟的,虽经公安局严厉查拿禁,但也是屡禁不绝。麻将牌也在禁止之列,但老太婆斗纸牌他不管。
当时小站这地方不大,但邪教门倒是不少,有天地门、太上门、如意门等,还有信五大仙的,什么狐黄白柳灰都信,还有专门顶仙的,无异于一神仙世界。小站还有个老头会,也就是集资打白事会,先死先得,简直就是奇葩。
“新农镇前新稻香,黄云拂水秋波长;时当秋获老农喜,检点䎱稏皆登场”。这是李庆辰诗集《醉茶吟草》第二卷中的《新农镇观获稻歌》。人们都说小站这个地方所产稻米质量好,这是因为小站地区在自然环境上适合水稻的生长。御河水内含有淤泥和腐殖质较多,水质好,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丰富、充足的养料,对提高米质和产量有着很大的关系。“用御河水浇过稻田后,田中淤下很厚的一层红色淤泥,比上什么肥料都强。”但是人们通常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种子。
当时的小站稻虽然高产,但不一定像现在的好吃,因为李庆辰在第三首中有“新农田广收粳稻,古淀波深采芰莲”一句,所以推断小站当时种植的水稻是粳米。颗粒呈椭圆形或圆形,颜色蜡白且半透明,因其淀粉含量较高,口感不好,不易消化。所以大公报《津郊调查之十:如此之小站》中提到,小站当时还种了少量的江米和日本稻米。
据1937年11月27日庸报《小站稻畅运津》中说:“小站稻米分二种:一曰长王米,一曰蚌珠米。长王米系小站产地本种,粒身较长,光泽精润,油质丰饶。十数年前小站稻新作物登场时,尽系长王一种,惜吾国农民墨守旧规,不事改良,致长王米种逐年退化,米质不佳,收货依年递减。故于十数年前,某著名米商由日本採来精良米种,试种于小站稻地,结果收获倍增,故近数年来各佃户为增多产计,大多采用新种,籍获得利”,每亩能增产二三石不等。
日本人的肠子只能吃大米,所以对水稻的产量和育种技术相当重视,我们从1937年朝鲜总督府农林局所编《主要农作物耕种梗概调》可见一斑。当时小站的日本稻种获得有几个途径,一是通过自由贸易获得的,一是由我国东北、冀东一带日侨聚集地传过来的,一是在海河对岸军粮城有日本人开设的农场。总之,当时的小站虽然种植日本优质稻米,如银坊、陆羽、水原等品种,但是获得稻种有限,所以种植面积不大。
小站稻原产地另一品种“蚌珠米也是,此种米粒身短圆,光泽耀目,米质尤佳。复经机器碾皮,其质不次于长王稻米,价格尤属低廉,市民多乐用之,产区之种长王米者日渐稀少。近年来欲求真正之长王稻米于本埠米肆中,恣不可得也。”④
在日本米谷统制之前,每年七八十万包小站稻是怎么运销的呢?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海河运抵津门,大小船只所载尽系稻米,码头争卸尤其忙碌。市民亦皆以争食新米为佳,结果供销两旺。还有一种为仓储,如斗店、货栈、银行仓库等,皆以新米集中上市价格回落而收储,待青黄不接时高价出售。每包稻米货利不少于二元之谱。
还有一些大车店,见利润丰厚,也做起稻米生意。原是那些小门小户,新米下来用大车或小船运到天津,人生地疏,两眼一抹黑,零售等不及,批发又被粮商压榨,于是大车店的老板出了个主意,说我这里可以存货,也可以给你代售。双方谈定价格,农民赶大车或撑船回家了,大车店无形中就蜕变成粮栈,人称“稻米栈”,多设在南门外,一共有九家,逐渐组织完善,规则严谨,信誉可靠,购销双方建立了稳定的机制。因此银钱业也看到了商机,主动上门联系抵押贷款业务,并为客户提供担保及水火保险等。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他们把天津作为向华南进攻的最大的兵站和后勤补给基地。在粮食方面,一面利用米谷统制会加紧控制,一方面提供优质稻种力图扩大生产,汉奸组织也积极配合,推广日本稻种与旱田改成水田并举。当时小站有稻田三千顷,年产水稻七八十万包,悉被日本三井、三菱、精谷三家公司收购殆尽,运往前线。
华北沦陷期间,日本人为了扩充军用大米,把小站列为军事管理区,并且派来很多农业专家,从事改良小站稻的改良工作,日本人对小站水田也费了不少心思。单就产量而言,改良后的小站稻,从亩产一百多斤,提高到七八百斤;稻田由人力灌溉,也都改成了电力。“只可惜八年中所出的稻米并没给国人吃。至于今日的小站稻米,虽仍以小站稻来标榜,其实这些稻米,正是纯正的日本米种,已不能保持当年小站稻的原质”了。⑤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小站的营田计有9.7万亩,以日据时期日本人统计数字,最高年产量为7760万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产量。日本投降后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但仍能保持亩产800斤的产能。
1948年,记者到小站采访,“一进了小站北门,首先看到的是袁世凯当年练兵的营地,和日寇遗下的电场遗痕。六棵矗立的洋灰柱子上面,还有残存的电线瓷轴。由这些仅余的陈迹,可以追忆起许多有关小站的辉煌历史,当地人更能津津乐道的告诉你,一些他们祖先开辟小站营田的经过。一块白墙上横写‘天津县小站镇’几个黑字。”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只知道向人民敲诈勒索,从来不关心农业生产。春旱、海水倒灌,咸水危害,秋涝水排不出去,大片土地被淹。水稻品种混杂退化,栽培技术落后,各种病虫害发生严重。闻名中外的小站稻生产仍然得不到发展,单产也一直很低。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生产的积极性也空前的高涨,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大力兴修水利,提高了排灌能力,解除了咸水的危害。”“到五十年代中期,已提高到1800-2000墩左右,并且普遍推广使用上了“水源”三百粒,淘汰了解放初期使用的“金刚”稻种,实现了优种化,使单产量不断增加,米质不断提高。”⑦
我们舌尖上的记忆,大致就是这一时期的小站稻。

注释:
①(《津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胡林茂《小站和小站稻》)
②(《周武壮公遗书》卷七·屯政编·《开河兴屯请借米价禀》,第675页)
③(大公报,1931年1月27日,《津郊调查之十:如此之小站》)
④(庸报1937年11月27日,《小站稻畅运津》)
⑤(益世报1947年11月9日,《小站的稻米》)
⑥(益世报1948年1月21日,《小站劫后现状》)
⑦(津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1-3辑 胡林茂《小站和小站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