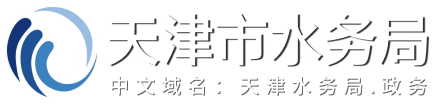小站是天津市南郊区的重镇之一,它以盛产小站稻米而名驰中外。
小站位于天津市东南部约七十华里,马厂减河北岸,东临渤海湾的西岸三十余华里,南过大港区。这片土地原是退海之地。据考古工作者实地调查,发现在南郊区有两条南北方向的贝壳堤。一条是始于白塘口,北到海河北岸的张贵庄,南经巨葛庄、沙井子,至黄骅市的武帝台。另一条是始于西泥洁,南经邓岑子,新开路、上吉林,一直到歧口。据科学院对在巨葛庄贝壳堤中挖出的铁农具,铜箭头的考证。证实是战国遗物,距今已有三千四百余年;而对邓岑子贝壳堤进行化验证实距今只有一千六百年。贝壳堤是海潮将海里的贝壳堆积而成的,是原来的海岸线的遗迹。四千多年前,约在原始公社时代的末期,现在天津市区内海河起点的“三岔河”口是海口,海河流域各河流(某些时期还包括黄河为主流)都从这里注入海中。这些河流里所挟带的泥沙就都淤淀于河口,日久天长变为洼淀形成陆地,使海洋线渐向东延伸到白塘口,又到泥洁。这两条贝壳堤分别是当时的海岸线。所以说这片土地是由海积与河流冲积物逐步形成的。
小站的形成
清朝同治十年(1871年)当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时候,在马厂驻兵,并在新城、大沽修筑炮台。为了来往交通方便,修建了一条长达一百多里的路(即今马新公路),沿途每隔四十里设立一大站,每隔十里设立一小站以供来往官兵休息之用。今天的小站镇,就是当时的一个小站。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的部下统领周盛传(与李鸿章同乡)带兵来此地电田练兵,并挖了马厂减河,垦荒植稻,从此小站就开始兴旺起来。
周盛传(字薪茹,晚号北海老农)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封建大地主家庭,二十一岁时(成丰三年)同他的兄弟们一起组织“国练”,抗击太平天国的军队,因他死心塌地地为封建统治者卖命,当了军官,镇压过捻军和其他农民起义军。同治十年李鸿章派他率领其部(称“老盛军”)九千余人,从安徽合肥出发开往北方镇守大沽口。来北方后,清政府因其军队系乌合之众,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不能镇守大洁口要塞。于是又调往新城后方操练,再西迁至小站。周盛传将其部队“老盛军”十八个营,分片驻扎,设立了营盘。今天的前营、后营、正营、老左营、西右营、盛字营、传字营······等地的名称就是起源于“老盛军”的营盘番号。
周盛传屯兵小站以后,他见到小站地区漫地旷野,前代又有过屯田的传统经验。同时,发现海水日涨落二潮,河水的水位上升,只要挑开引河,就可引水灌溉农田,对开荒耕田十分有利。当时正值没有战事,比较安定,正适合屯田练兵。因此,他查看了水源,勘测水位,动用了“老盛军”的全部人马,于一八七五年动工开挖马厂减河。上游西接于靳官屯闸中,引南运河水入马厂减河,下游向东流经新城至西大沽流入海河。全长一百七十华里。在施工中,由于经费不足,军饷发生困难。士兵们进行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吃不饱,曾一度发生兵变,士兵们大批逃亡,工程停滞了二年之久。后来周盛传又招兵买马。并得到了李鸿章的赞助,调来了一部分淮军,继续挖掘马厂减河,于一八八〇年基本告成。马厂减河修成以后,引来了南运河水(也称:御河水)。由于小站地区土地盐碱,适于种植水稻,同时老盛军士兵多为南方人,对种植水稻经验丰富,因而就开辟为水稻田区。当时的垦植单位是以营为基础的,每营是种的土地为十三顷(折合一千三百亩)。据《周盛传传略》中记载:“七年、辛巳,四十九岁。(一八八一年)······我军于乙亥年移屯新农镇(即:小站镇),即以试办电是之事,频年以来,逐渐推广,计自新城一代上至驻军之析,成熟者不下六百万余面,遂将距营较远之处招来民人领种。自去年十月至今年二月,共领种熟田一万四千余亩,每面分别等值,酌收大钱二百文、一百文不等。车屋等项照时估价。······数年以来,屯是之事至此稍一结束”。
随着马厂减河的开挖,稻田区的开垦扩大,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因此,各地一些逃荒、要饭、扛活卖短的穷人听说小站“扣民人领种”稻田,便纷纷汇集到小站地区谋生,有的则自己开垦稻田。由于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商业活动的发展。光绪三年(1877年)由于驻军官兵和当地百姓的生活需要,周盛传就曾在小站修城门、盖住宅、修街道,并由静海县、唐官屯、独流镇等地招来商贩人员,由周盛传供给资金,开设商店,贩运货物,以供小站军民的生活需要。一八八五年,周盛传病死。(被清统治者封谥为“武壮公”)其兄弟周盛波继任周盛传的官职后,又重整街市,曾在小站镇修建大街,并盖民房五千余间,又设了招商局,修建了会馆、戏楼作为集会和娱乐的场所。至此,小站由原来的人烟稀少开始兴旺起来,人口亦随着日益增加,相继也出现了工、农、仕、商、学、兵各种阶层。小站也就逐渐地形成一个社会组织。小站曾因老盛军开荒垦田,被命名为“新农镇”。但没有被军民们承认,仍称为“小站镇”一直流传至今。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盛军被调往安东(丹东)和日军作战,全军覆没。
小站地区的稻田,由于它开始系周盛传的老盛军所开垦,因而,它一开始,就成为官地。土地一部分为盛军士兵自植自种,所得粮食补助军队的军饷;一部分为朝廷享用;mm 还有一部分租给当地农民耕种,盛军走后,许多土地因无人耕种而荒废。为了不使这些土地长远荒废,清政府发出告示,要把土地分给百姓领种,但大部分土地被退职的官僚和士兵所领。从此,小站地区的土地开始变为官有、私人使用制度。凡领取土地耕种者,不论土地多少,均必须向官府交纳地租,每亩交银七钱,土地许兑不许卖。但随着封建社会中土地兼并的进行,一些小土地使用者的土地又渐渐地集中到少数封建官僚、大地主手中。他们或雇佣外地逃荒的农民耕种,或把土地再租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向佃农收“小租”,因此小站地区的劳动人民要受官府、地主的双重地租剥削。
一九八六年成立小站营田管理局招致附近农民和一部分遣散士兵耕种,每亩交六钱至一两租银不等。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曾一度被德国占领,一九〇五年在小站设立垦务局办理荒地招垦事宜,后又与营田局合并,这时小站稻面积七八万亩,小站已小有名气。
小站稻的渊源与兴衰
小站地区的特产“小站稻”,久以产量高,米质好而驰名中外,虽然它作为名贵产品名扬海内外只是近百年的事,可是其种植源远流长。
早在宋代,宋辽对峙时期,为了防辽入侵,端拱二年(989年)沧州节度副使何承矩向宋太宗做“为实边之要策”上书建议。他说应该在顺安翘(今高阳县以西)东到渤海湾的三百余里,宽一百七十里的广大区域内,开沟、屯田,并雍塞淀泊制造土地。这样就可以不必“发兵广戍”,就能“收地利以实边,设险固以防塞”(见《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直隶》《安州》)。宋太宗听了他的报告后,立即委派他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黄懋为助手,调动一万八千名士兵供他调遣。在十多年中,从雄州、郑州、霸州直到包括现在的小站地区在内的渤海滨,总共兴建了六百里的堤堰。开了不少水渠,建了不少闸门,大面积地开垦了稻田。《宋史》上赞美何承矩的功绩说:“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且有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同时又构成了一道“屈曲九百里”的险固的防辽屏障。还沿界河(海河)设了一百多个寨和铺,即边防哨所。现在的泥洁、双港、三合、葛洁等地都是当时的寨、铺。但他们在第一年种稻时引用的是南方稻种,由于没有掌握北方气候的规律,失败了。但后来终于获得了成功。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初年种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气迟。江东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种籽令种之,是岁八月,稻熟”。他们的实践,为以后北方水稻的种植提供了经验。这是小站地区开发于历史文献的最早的记载。
元朝初年,由于蒙古族统治了中国,开始他们不注意农业生产,宋代所垦稻田大都荒废。直到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据《元史·武宗纪二》记载有:“摘汉军五百,给田十千顷,于直沽沿海口屯种。”至泰定天历时(公百1324年至1328年)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虞集曾上书建议:“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于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未能被采纳,但他说的方法却一直被后代在滨海地区垦田的人们所遵循。
到了明朝,当统治者由于采取了“寓兵于农”的政策,广泛采用了军屯和民屯的方法,小站地区的水稻生产又有了恢复,发展进入了一个兴旺时期。从万历年间至天启年间先后二十多人向皇帝上书或在小站地区实地开垦屯田。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汪应蛟的贡献。汪应蛟是明朝万历年间保定巡抚,也是一个农田水利学家。对于小站地区的农田水利开发来说,他曾创立过重要的业绩。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汪应蛟来到天津小站地区。开垦稻田。曾上书“臣窃见天津葛沽一带咸谓此地从来斥卤不耕种。······臣窃以谓此地无水则卤。得水则润,若以闽浙濒海治地之法施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为稻田。······”“至今开始买牛制器。开垦筑堤,一时并兴。计葛沽、白塘二处耕种共五千余亩,水稻两千亩,其粪多力勤者,亩收四、五石······”“于是地方军民始信闽浙治地之法可行于北海。”垦田筑堤一时大兴。汪应蛟把这次尝试的结果报告了神宗,并提出了一个开垦七千顷、年产二百余万石的庞大生产规划。其中特别强调了“用军垦田,以田分民”和招募边地殷实居民”及“南人有资本者听其分领承种。”神宗批准了他的规划。于是汪应蛟调用了“海防官军万人分田垦种”,一共沿海南岸开辟了十个“围”(即何家圈围、白塘口围、双港围、辛家围、羊码头围、咸水沽围、东泥沽围、西泥沽围、盘沽围、葛沽围)。所谓“围”,就是用“闽浙濒海治地之法”,垦荒造的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从海河开一条“用干”,涨潮时将甜水引入,南开一条“排干”,落潮时将咸水泄入海河,在适当的地方建立一些桥梁、涵闸,干渠的外面培高为埝以防沥涝,两条干渠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围”。围内再开支渠、毛渠以资灌溉。汪应蛟的业绩之所以是重要的,就在于他所开辟的“十围”,基本上奠定了现在小站地区北部沿海河一线约二十五公里长的地段内全部耕地的基础,为小站地区改良盐碱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大科学家徐光启也曾先后四次来天津小站地区致力于垦田植稻,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亲自沿海河踏勘土地,在灌溉技术和治田上他认为:“稻田用水,随时随地,不拘一法,括之以两言,蓄与泄而已。”“灌田者先须以水遍过,收其热气,旋即去之,然后易之新水。”在整地上,他指出了当时存在的弊病:“粑者多不求细熟平整,粗块雍泥,凸则曝日先燥,洼则注水过深。”他并与当地老农研究改进了施肥措施,解决了南种北引问题。
公元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后,满族人统治了中国,清朝初年,由于战乱社会经济遭到破坏,许多地方(包括小站地区)田园荒芜,经过了约百余年后,生产才渐渐恢复,在小站地区开垦庄田的又多起来。雍正五年(1727)怡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又在小站地区海河沿岸大搞屯田。并设立了一个“水利营田府”,设立了营田观察使等官职。他们搞的屯田工程主要是修复明代汪应蛟的“十围”(这次建的十围地方不与汪的完全相同)。
清咸丰九年(1859)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督兵大沽海口,在咸水沽、葛洁一带挑沟建闸,引海河水灌溉,种植水稻。这时小站地区的水稻面积又有发展。
清同治十年(1871年),周盛传率领老盛军进驻马厂,后又开发小站。具体情况详见前词“小站的形成”部分。这里只提一下小站稻出名的原因。
周盛传在小站还没开发种铝以前,葛洁稻就已负盛名。清朝时乾隆《天津县志》卷十一附《营田》中曾记述,明末清初时,葛洁所产的稻米,质量甚佳,几与南方的水稻良种“白玉塘”齐名。清周楚良《津门竹校词》中作诗赞美,诗云:“作粥葛洁稻粒长,汁滤晶碧类琼浆······”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崔旭在《津门百咏葛活》中亦有诗云:“满林桃杏压黄柑,紫蟹香粳饱食堪。最是海滨好风味,葛沽合号小江南。”小站地所产稻米米质好,这是因为小站地区在自然环境上适合水稻的生长。这个地区原是海积与河流冲积平原,地处海河流域的九河下箱,当时有充足的水源,虽然土壤含盐量较高,但前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已经总结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以水治盐,开渠引水”的水淹种稻技术。(当时的海洋水质也很好)。自周盛传开发小站,挖通马厂减河,引来御河水(南运河水)以后,使小站地区成了一个南有马厂减河、北有海河两个水源的稻田区,不但水源充足了,另外,御河水(南运河)内含有淤泥和腐殖质较多,水质好,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丰富、充足的养料,对提高米质和产量有着很大的关系。据当地老农回忆说“用御河水浇过稻田后,田中淤下很厚的一层红色淤泥,比上什么肥料都强。”所以小站稻米以粒大饱满,状若珠玑,蒸饭煮粥香气扑鼻,引人食欲而出名。
综合上述材料,从宋代以后各个朝代都出了不少“屯臣”在小站地区垦荒植稻,对小站地区的水稻种植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某些原因,当这些屯臣或军屯的部队离开以后,这些已开垦的土地,部分就随之荒废,始终得不到大面积的发展巩固,热面他们的垦荒植稻的实践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小站地区种植永精的历史,如从宋代端拱二年(989年)沧州节度副史何承短为防辽入侵留下田层荒植稻算起,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如自汪应较在小站附近的葛洁、白塘口种稻,后又开辟“十围”,基本奠定了现在小站地区以北部沿海河一线约二十三公里长地段内全部耕地的基础算起,至今有三百八十余年。但自周盛传电田小站,一八八〇年挖通马厂减河,使小站稻名扬中外才只不过百年的历史。
“小站稻米”出名以后,但在解放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华北,为掠夺军粮,实现“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在小站地区兴修了一些水利,进行了一些水稻新品种的选育和栽培技术的研究。推广使用“银坊”“水源”等优良品种,提高了小站稻米的质量。但日军对小站地区的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进行凶残的掠夺。一九四〇年日寇在小站设立了“军谷公司”强行收购稻谷,一九四一年又改为“米谷统治会”,对小站地区生产的米谷完全控制了起来,老百姓一粒也不许吃,不许私卖,强行压价收购,所收的稻谷一律要交“米谷统治会”。一经发现农民私吃、私卖,便残酷地加以杀害。由于日寇的法西斯统治,农民们也以各种形式加以反抗。水稻生产毫无起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只知道向人民敲诈勒索,从来不关心农业生产。春旱、海水倒灌,咸水危害,秋涝水排不出去,大片土地被淹。水稻品种混杂退化,栽培技术落后,各种病虫害发生严重。闻名中外的小站稻生产仍然得不到发展,单产也一直很低。
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生产的积极性也空前的高涨,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大力兴修水利,提高了排灌能力,解除了咸水的危害。仅以马厂减河地区而论,解放前当地只有桥闸工程25处,而且破烂不堪,经常发生旱涝灾害。解放后,从四九年至五七年仅八年的时间,就新建和修补桥闸涵洞1588处,国家投资达217万元。而且发展了电力事业,建有大型扬水场四座,随着水利兴修的发展,大量的荒地被开垦,水稻的播种面积不断地扩大。在水稻的栽培技术和选育优良品种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解放前,当地群众的习惯是“稀苗大穗”,每亩插秧仅800墩左右,到50年代中期,已提高到1800~2000墩左右,并且普遍推广使用上了“水源”三百粒,淘汰了解放初期使用的“金刚”稻种,实现了优种化,使单产量不断增加,米质不断提高。(但由于水质不同,御河水质较好,论米质仍以用御河水为主的,马厂减河两岸所产的水稻米质最佳。)
我们把解放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水稻生产的发展与解放前的一九四八年做一对比。解放前水稻的播种面积仅14万亩,亩产量425斤。解放后的一九五三年总播面积已扩大到18.38万亩。亩产量提高到701斤。一九五五年播种面积达到21.56万亩,亩产739斤。到一九五七年播种面积已达到26.44万亩,亩产657斤。比一九四八年的播种面积扩大了88.9%,亩产增长了54.6%。由于播种面积的扩大和亩产量的提高,水稻的总产量增加速度更快。如果以解放前四八年的总产量5950万斤为100的话,则一九五三年以后逐年增长的情况是:

但到了一九五八年,情况有所变化。马厂减河上游和海河上游兴建了许多蓄水工程,广泛地发展了灌溉事业。引水灌田,发展水稻生产。仅以现在的天津地区为例:解放初全市(含现在的五县)水稻的播种面积只有35.04万亩,其中小站地区就占17.24万亩(占49.2%)。到一九五八年,全市的水稻面积扩大到153.7万亩,而小站地区只有15.70万亩(仅占10.2%)。由于上游用水多,下游的水源就大量减少。再加上开挖独流减河,切断了马厂减河,中断了南运河、马厂减河直接来水,使马厂减河两岸水源断绝,无水种稻。自此以后,小站地区由原来的两个水源只剩下海河一个水源,用水情况可谓每况愈下。当时又赶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再加上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挫。致使五八年至六二年的水稻生产下降到解放初至五三年前的水平。
为了解决马厂减河沿岸的缺水问题,必须把海河的水南调。于是在区政府的领导下,又开挖了洪泥河,疏浚了月牙河,并建立了双羊渠,后营、南义、东花园、葛沾、东泥洁,六个扬水站,形成了深渠河,使用了机灌,电灌代替了龙骨车和柴油机,扩大了灌瓶面积,又推广使用了“白金”“黄金”等优良品种,促进了农业生产,使水稻生产恢复到50年代中期水平。到六三年播种面积20.68万亩,亩产626斤,总产量是12947万斤。到六五年,桥种面积23.87亩,商产是915斤,总产是21841万斤,超过了五七年,达到了小站地区水稻种植史上的最高水平。从六五年以后,直至七一年的六年中又持续的稳定高产,平均每年的播种维持在23.16万亩左右,平均亩产696厅。这一段时间是小站稻生产的最兴旺时期。(从解放后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一年的二十二年中,稻谷总产量累计共达299468万斤。)
小站稻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大批优质稻米对提高小站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为支援兄弟省市发展水稻生产,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的水稻良种,并应邀派出大批农业技术人员,到一些兄弟地区传授水稻栽培技术,为我国水稻生产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由于水源情况的变化,在60年代后期海河水量就逐年减少,特别是进入70年代,水源不足的矛盾更加严重。到一九七二年,上游来水基本断绝,又遇上了数十年没有过的特大干旱。上级农业生产领导部门已作了改种旱田作物的决定,但当时农民种稻心切,又受陈伯达“无水也种稻”谬论的影响,一些社队违反了客观条件的变化规律,仍坚持种稻,全区播种水稻面积69951亩,插秧后,因无水,有一多半稻田,水竭苗枯颗粒无收,平均亩产仅有84斤。至一九七三年,小站地区的所有稻田几乎全部被迫改种旱田作物。后来又一律禁止种稻,就是有的地方有自备水源,能够种稻的,也不允许种。有的偷着插上了秧,也被强令拔下来,全部改旱。但也还是有一少部分地块偷着种上了水稻。全区每年充其量不过几千亩。至此,闻名已久的小站稻就已销声匿迹,濒临灭绝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结地区人民总结了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恢复和发展小站稻生产,首先必须抓住自力更生解决水源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天津市委也提出了要自备水源,恢复水稻生产的要求。小站地区广大农民积极响应,他们利用坑塘洼淀,沟渠河网,在雨季蓄水,并且充分利用城市污水,为水稻生产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水源。另一方面,他们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种植方法,扬长避短,节水种稻。小站稻的生产又有所恢复。一九七八年种稻三万八千多亩,平均亩产384斤;一九七九年播种面积九万二千多亩,平均亩产653斤;一九八〇年播种面积扩大到十一万七千亩,平均亩产536斤。但到一九八一年天气又严重干旱,一至六月份降雪量仅有74毫米,为常年的13%。在水源极缺的情况下,有的队又不顾具体情况的变化,盲目种稻,结果全区播种的六万四千多亩水稻,平均亩产只有283斤。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近三年内,全区水稻的播种面积分别是:二万四千亩、二万七千亩、三万四千亩,平均亩产分别是:350斤,651斤,720斤。
以上是“小站地区水稻”生产的渊源和兴衰过程及现状。从栽培历史上看,小站稻的生产和发展,除去社会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水源的变化情况。从其变化的规律中,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凡是在水源有保证的情况下,生产就会获得较大的发展。反之,就会下降。
因此,虽然小站地区的土地,气候适宜水稻生长,群众又有着种植水稻有优良传统和丰富的经验,小站稻的生产也曾获得过很大的发票,至今小站地区的人民还留恋着那“鱼米之乡”的兴旺时期,但现在的小站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改变了,在目前缺乏水源的情况下,要使水稻生产再恢复到五、60年代的水平是根本办不到的。广大群众通过几年来的实践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可是广大群众和农业技术人员的实践也证明了,在没有外来水源的情况下,并不是一点也不能种。只要从实际出发,合理地利用当运自然资源,发挥本地区的优良传统和技术优势,还是可以适当地种植一定面积水稻的。前面提到在70年代末期,部分农民曾因地制宜利用坑塘洼淀、沟渠河网在雨季蓄水自备水源种稻,近几年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又出现了把养鱼、养苇同植稻结合起来的新办法,并选用了“中丹二号”“红旗16号”“垦丰5号”“丰锦”“白金”等优良品种。因此,八三年,八四年两年,虽然耕种面积不大(三万亩左右),但亩产较高(700斤左右)。
另外,近年来由于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受水源的限制,一.些农业科技人员在节水种稻的研究上已取得不少的成功经验。
再从客观水源条件分析也存在这个可能。小站地区年降雨量平均558.4毫米,但降雨季节不均,在五月前降雨很少,大部分集中在六至九月间,常年为448.8毫米,约占全年降雨量的70%。七至八月间,比较多,常年为335.4毫米,约占全年降雨量的62%。据统计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有七年在七月上旬前下了大雨,此时正是水稻生长发育最旺盛,雨水量最多的时期。但常出现暴雨成灾,大量雨水被排掉。而小站地区由于多年种稻,河渠成网,其中可用来蓄水的二级河道就有八条,可蓄水540万立方;再加上我区有新建小型水库13座,可蓄水534万立方米;坑塘洼淀11处可蓄水42万立方米;共计可蓄水1116万立方米,排污河还有一定数量污水可以利用。如果把这些条件都充分合理地利用起来,并推广节水种稻的栽培方法,水稻生产在现有的基础上,还是可以适当再发展一定面积水稻的。